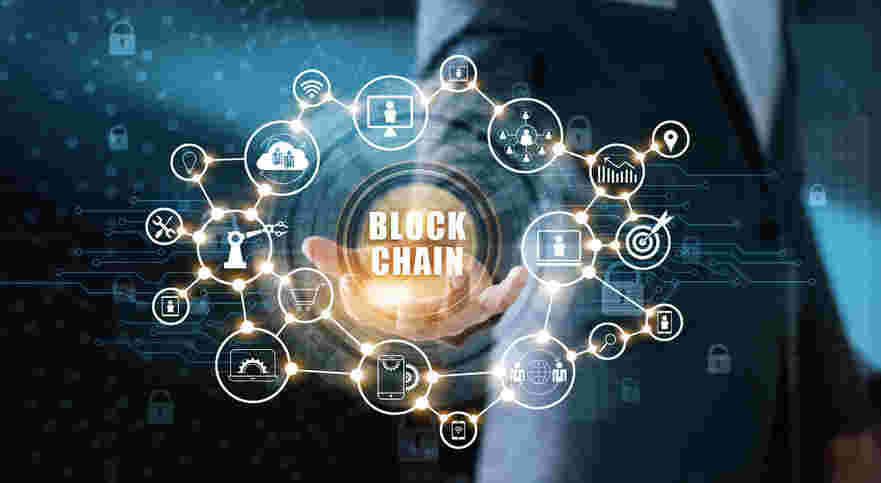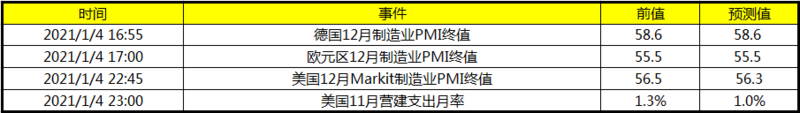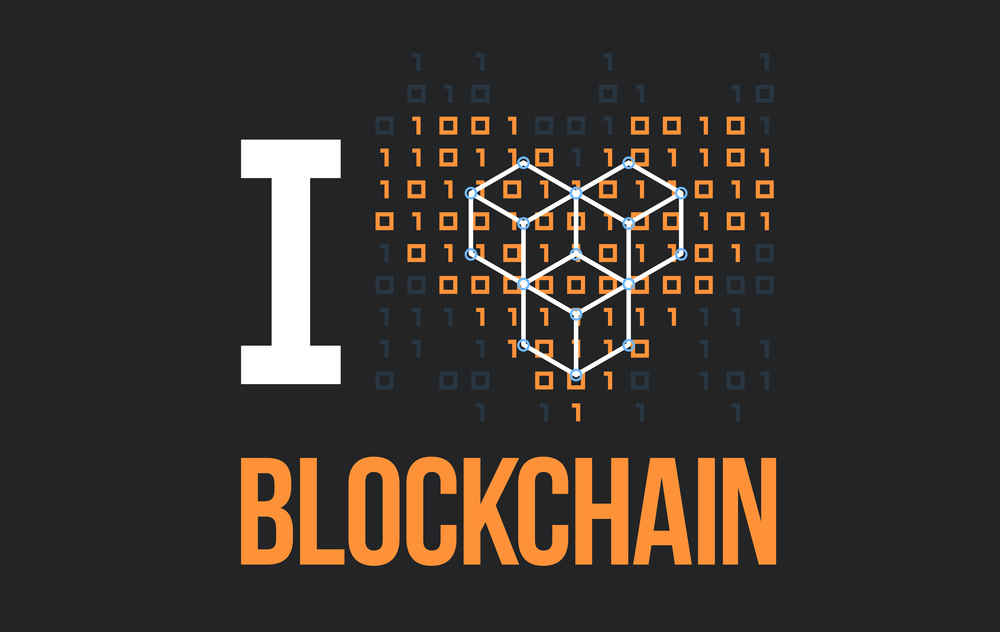《香港外汇》欧洲各国首脑们的下一个大错
原标题:《香港外汇》欧洲各国首脑们的下一个大错
在当年架构欧洲货币同盟时,欧洲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并没有把所有隐含后果一一想透,这就有了后来的几大设计缺陷。更有甚者,吃一堑却未长一智,如今,他们的后继者正打算用同样的方式打造欧洲政治同盟。
金融危机的逻辑迫使欧洲进一步加深一体化,这意味着,需要为政治表达找到一种新机制。恰恰就在危机之前,欧盟普遍受到“民主不足”的诟病。如今,许多欧洲人都因痛苦的财政瘦身而对欧盟破口大骂,上述诟病声浪日高,让欧洲各国首脑们觉得必须马上着手应对。
屋漏偏逢连夜雨,欧洲其实还有另一个不足:政治领导力的不足。上世纪中叶那些半神式的领袖——丘吉尔、阿登纳、戴高乐——如今后继无人。欧盟让民众联想到的首先是暮气沉沉的官僚作风和技术官员主导的冰冷理性。
对于这个不足,欧洲官场想出来的应对办法是改革欧盟委员会,让其变得更民主。欧盟委员会现任主席巴罗佐建议,在下届欧洲议会选举之时,让意识形态立场相近的政党结成更紧密的政治“派别”,联合提名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这样一来,选民就可以更直接地选举新一届欧盟行政首脑。他们会觉得好像在选举一届政府一样。而政治家们为了胜选,就有动力去提升自己的感召力。
这一倡议得到一些名流的支持,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是因为,该方案显然不会给各国政府带来任何实际的权力损失,它已经获得了一些接受度并且似乎易于实施。但那并不能使其成为一个好主意。尤其是,要把现有的欧洲政治“派别”装进一个两党制的筐子里——泛社会民主党和泛“人民党”——这种做法有大问题。
议会两党制出现于19世纪的英国。选民只要在下院两党中二选一,再由多数党指定首相。当代英国漫画Iolanthe如此表达这种“体制自信”:每个活着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子或丫头,不是一个小自由党,就是一个小保守党。可是,如果并非每个小子或丫头生出来就是那样,又当如何?
按照稳定的英国模式,如果哪个党过于极端,在下届选举里它就会被迫离开权力中心。两党对立不是什么坏事,但按惯例,两党通常都有意愿寻求具备广泛社会共识的政策方案。然而,这种制度后果并不一定会出现(哪怕在当今的英国,它大概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英国立法者喜欢向别国推广这一模式。在前英国殖民地,这种模式别具吸引力,尤其是在新近独立的一些非洲国家。但推广的结果是灾难性的。那里的公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非得把自己的政治偏好装进简单的左右二分法。实际上,那里的政治往往还是根据昔日的部落、族群矛盾来站队。
美国今日的现实也无法令人信服,两党竞争有利于消弭分歧、壮大政治中坚派。恰恰相反,党争有时会让一个党派走极端。
“两党意味节制”这个命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成立,那就是:主要的政见分歧是对再分配的喜好程度。左翼党想要多搞点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右翼党则想少一点,但双方都必须自我节制,为了吸引中间选民,两党最终变得似异实同。
然而,在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新政治,在这种新政治环境下,不论左右翼都担心,外部竞争或影响将限制其塑造政治选择的能力。它们的主要政治偏好变成了抵抗那些外部威胁。传统的左-右分野已经行不通了。
人为地将欧元区政界分成左派右派会引发新的争斗,并且激化老的、关于再分配的争斗。唯一能把左派团结起来的是“更多再分配”的主张——但是,分配给谁,按什么机制分配?
西班牙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之间的共性,也不再比它们各自同国内民族主义党派之间的共性更显著。各个意识形态阵营很可能会沿着复杂的民族界线而分裂——而民族界线也将在追求魅力的政治竞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搞不好,这套方案没能催生新的丘吉尔和阿登纳,反而唤醒了新的希特勒和斯大林。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模式就诞生在欧洲的地理中心,诞生在语言、文化和宗教多元性极大的一个政治试管里:瑞士的协调民主模式。在瑞士体制里,若干个政党参与竞争,但并不是为了独占政权。在政府里,各大党派都有代表,因此都必须准备妥协。联邦政府成员有时忠于地区利益,有时看重意识形态价值,在决策时却无一例外需要谈判妥协。
旨在选出广泛而均势政府的瑞士方案容易导致无聊乏味的政治生活。很少有人知道谁是瑞士年度轮值主席,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政治明星靠的是让支持者变得激动、极端化,从而达到动员目的;日常政治则相反,需要保持低调,需要准备妥协。今日的欧洲不需要能够煽起民众狂热的传奇领袖,而需要能在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政治环境下工作的、受当地人民爱戴的领导人。